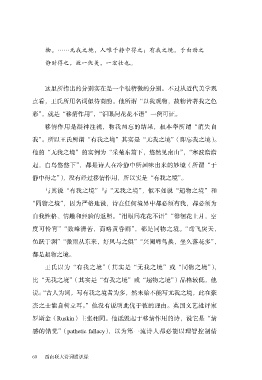Page 80 -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
P. 80
物。……无我之境,人唯于静中得之;有我之境,于由动之
静时得之,故一优美,一宏壮也。
这里所指出的分别实在是一个很精微的分别。不过从近代美学观
点看,王氏所用名词似待商酌。他所谓“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
彩”,就是“移情作用”,“泪眼问花花不语”一例可证。
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,物我两忘的结果,叔本华所谓“消失自
我”。所以王氏所谓“有我之境”其实是“无我之境”(即忘我之境)。
他的“无我之境”的实例为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“寒波澹澹
起,白鸟悠悠下”,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(所谓“于
静中得之”),没有经过移情作用,所以实是“有我之境”。
与其说“有我之境”与“无我之境”,似不如说“超物之境”和
“同物之境”,因为严格地说,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,都必须为
自我性格、情趣和经验的返照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”“徘徊花上月,空
度可怜宵”“数峰清苦,商略黄昏雨”,都是同物之境。“鸢飞戾天,
鱼跃于渊”“微雨从东来,好风与之俱”“兴阑啼鸟换,坐久落花多”,
都是超物之境。
王氏以为“有我之境”(其实是“无我之境”或“同物之境”),
比“无我之境”(其实是“有我之境”或“超物之境”)品格较低,他
说:“古人为词,写有我之境者为多,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,此在豪
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”他没有说明此优于彼的理由。英国文艺批评家
罗斯金(Ruskin)主张相同。他诋毁起于移情作用的诗,说它是“情
感的错觉”(pathetic fallacy) ,以为第一流诗人都必能以理智控制情
60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