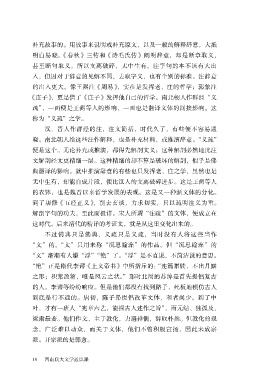Page 40 - 1957
P. 40
补充故事的。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,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,大抵
明白易晓。《春秋》三传和《诗毛氏传》阐明辞意,却是断章取义,
甚至断句取义,所以支离破碎,无中生有。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
入,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,去取字义,也有个别的标准。注辞意
的出入更大。像王弼注《周易》,实在是发挥老、庄的哲学;郭象注
《庄子》,更是借了《庄子》发挥他自己的哲学。南北朝人作群经“义
疏”,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,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。这
称为“义疏”之学。
汉、晋人作群经的注,注文简括,时代久了,有些便不容易通
晓。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,也是补充材料,或推演辞意。“义疏”
便是这个。无论补充或推演,都得先解剖文义;这种解剖必然地比注
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。这种精细的却不算是破坏的解剖,似乎是佛
典翻译的影响。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、庄之学,虽然也是
无中生有,却能自成片段,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。这是王弼等人
的衣钵,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。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。
到了唐修《五经正义》,削去玄谈,力求切实,只以疏明注义为重。
解剖字句的功夫,至此而极详。宋人所谓“注疏”的文体,便成立在
这时代。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,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。
不过佛典只是佛典,义疏只是义疏,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
“文”的。“文”只用来称“沉思翰藻”的作品。但“沉思翰藻”的
“文”渐渐有人嫌“浮”“艳”了。“浮”是不直说,不简洁说的意思。
“艳”正是隋代李谔《上文帝书》中所指斥的:“连篇累牍,不出月露
之形;积案盈箱,唯是风云之状。”那时北周的苏绰是首先提倡复古
的人,李谔等纷纷响应。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,死板地模仿古人
到底是行不通的。唐初,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,和者尚少。到了中
叶,才有一班人“宪章六艺,能探古人述作之旨”,而元结、独孤及、
梁肃最著。他们作文,主于教化,力避排偶,辞取朴拙。但教化的观
念,广泛难以动众,而关于文体,他们不曾积极宣扬,因此未成宗
派。开宗派的是韩愈。
18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