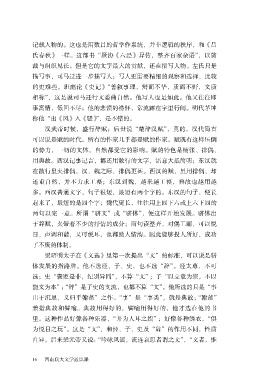Page 38 - 1957
P. 38
记载人物的。这也是用数目的哲学作系统,并非逻辑的秩序,和《吕
氏春秋》一样。这部书“厥协《六经》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”,以剪
裁与组织见长。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,还在描写人物。左氏只是
描写事,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;写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,比较
的更难些。班彪论《史记》“善叙事理,辩而不华,质而不野,文质
相称”,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。他写人也是如此。他又往往即
事寓情,低回不尽;他的悲愤的襟怀,常流露在字里行间。明代茅坤
称他“出《风》入《骚》”,是不错的。
汉武帝时候,盛行辞赋;后世说“楚辞汉赋”,真的,汉代简直
可以说是赋的时代。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。赋既有这样压倒
的势力,一切的文体,自然都受它的影响。赋的特色是铺张、排偶、
用典故。西汉记事记言,都还用散行的文字,语意大抵简明;东汉就
在散行里夹排偶,汉、魏之际,排偶更甚。西汉的赋,虽用排偶,却
还重自然,并不力求工整;东汉到魏,越来越工整,典故也越用越
多。西汉普通文字,句子很短,最短有两个字的。东汉的句子,便长
起来了,最短的是四个字;魏代更长,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
两句以完一意。所谓“骈文”或“骈体”,便这样开始发展。骈体出
于辞赋,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;而句读整齐,对偶工丽,可以悦
目,声调和谐,又可悦耳,也都助人情韵。因此能够投人所好,成功
了不废的体制。
梁昭明太子在《文选》里第一次提出“文”的标准,可以说是骈
体发展的指路牌。他不选经、子、史,也不选“辞”。经太尊,不可
选;史“褒贬是非,纪别异同”,不算“文”;子“以立意为宗,不以
能文为本”;“辞”是子史的支流,也都不算“文”。他所选的只是“事
出于沉思,义归乎翰藻”之作。“事”是“事类”,就是典故;“翰藻”
兼指典故和譬喻。典故用得好的,譬喻用得好的,他才选在他的书
里。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,“并为人耳之娱”;好像各种绣衣,“俱
为悦目之玩”。这是“文”,和经、子、史及“辞”的作用不同,性质
自异。后来梁元帝又说:“吟咏风谣,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,“文者,惟
16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