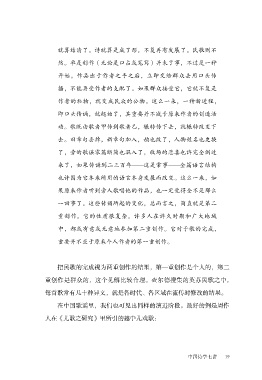Page 39 -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
P. 39
就算结清了。诗就算是成了形,不复再有发展了。民歌则不
然。单是创作(无论是口占或笔写)并未了事,不过是一种
开始。作品出于作者之手之后,立即交给群众去用口头传
播,不能再受作者的支配了。如果群众接受它,它就不复是
作者的私物,就变成民众的公物。这么一来,一种新进程,
即口头传诵,就起始了,其重要并不减于原来作者的创造活
动。歌既由歌者甲传到歌者乙,辗转传下去,就辗转改变下
去。旧章句丢掉,新章句加入,韵也改了,人物姓名也更换
了,旁的歌谣零篇断简也混入了,收场的悲喜也许完全倒过
来了,如果传诵到二三百年——这是常事——全篇语言结构
也许因为它本来所用的语言本身发展而改变。这么一来,如
果原来作者听到旁人歌唱他的作品,也一定觉得全不是那么
一回事了。这些传诵所起的变化,总而言之,简直就是第二
重创作。它的性质很复杂,许多人在许久时期和广大地域
中,都或有意或无意地参加第二重创作。它对于歌的完成,
重要并不亚于原来个人作者的第一重创作。
把民歌的完成视为两重创作的结果,第一重创作是个人的,第二
重创作是群众的,这个见解比较合理。查尔德搜集的英苏民歌之中,
每首歌常有几十种异文,就是各时代、各区域在流传时修改的结果。
在中国歌谣里,我们也可见出同样的演进阶段。最好的例是周作
人在《儿歌之研究》里所引的越中儿戏歌:
中国诗学七讲 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