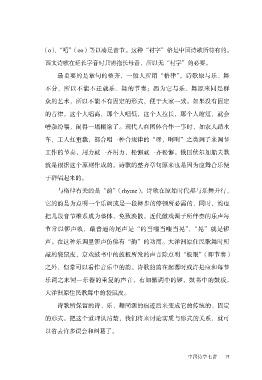Page 35 -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
P. 35
(o)、“唔”(oo)等以凑足音节。这种“衬字”格是中国诗歌所特有的。
西文诗歌在延长字音时只需拖长母音,所以无“衬字”的必要。
最重要的是章句的整齐,一般人所谓“格律”。诗歌原与乐、舞
不分,所以不能不迁就乐、舞的节奏;因为它与乐、舞原来同是群
众的艺术,所以不能不有固定的形式,便于大家一致。如果没有固定
的音律,这个人唱高,那个人唱低,这个人拉长,那个人缩短,就会
嘈杂纷嚷,闹得一塌糊涂了。现代人在团体合作一事时,如农人踏水
车,工人扛重载,都合唱一种合规律的“呀,啊啊”之类调子来调节
工作的节奏,用力就一齐用力,松懈就一齐松懈。俄国伏尔加船夫歌
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作成的。诗歌的整齐章句原来也是因为应舞合乐便
于群唱起来的。
与格律有关的是“韵”(rhyme) 。诗歌在原始时代都与乐舞并行,
它的韵是为点明一个乐调或是一段舞步的停顿所必需的,同时,韵也
把几段音节维系成为整体,免致涣散。近代徽戏调子所伴奏的乐声每
节常以锣声收,最普通的尾声是“的当嗤当嗤当晃”,“晃”就是锣
声。在这种乐调里锣声仿佛有“韵”的功用。大洋洲原住民歌舞时所
敲的袋鼠皮,京戏鼓书中的鼓板所发的声音除点明“板眼”(即节奏)
之外,似常可以看作音乐中的韵。诗歌的韵在起源时或许是应和每节
乐调之末同一乐器的重复的声音,有如徽调中的锣,鼓书中的鼓板,
大洋洲原住民歌舞中的袋鼠皮。
诗歌所保留的诗、乐、舞同源的痕迹后来变成它的传统的、固定
的形式。把这个道理认清楚,我们将来讨论实质与形式的关系,就可
以省去许多误会和纠葛了。
中国诗学七讲 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