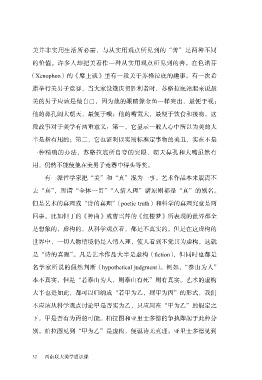Page 52 - 1959
P. 52
美并非实用生活所必需,与从实用观点所见到的“善”是两种不同
的价值。许多人却把美看作一种从实用观点所见到的善。在色诺芬
(Xenophon)的《席上谈》里有一段关于苏格拉底的趣事。有一次希
腊举行美男子竞赛,当大家设筵庆贺胜利者时,苏格拉底站起来说最
美的男子应该是他自己,因为他的眼睛像金鱼一样突出,最便于视;
他的鼻孔阔大朝天,最便于嗅;他的嘴宽大,最便于饮食和接吻。这
段故事对于美学有两重意义:第一,它显示一般人心中所以为美的大
半是指有用的;第二,它也证明以实用标准定事物的美丑,实在不是
一种精确的办法,苏格拉底所自夸的突眼、朝天鼻孔和大嘴虽然有
用,仍然不能使他在美男子竞赛中得头等奖。
有一派哲学家把“美”和“真”混为一事。艺术作品本来脱离不
去“真”,所谓“全体一贯”“入情入理”诸原则都是“真”的别名。
但是艺术的真理或“诗的真理”(poetic truth)和科学的真理究竟是两
回事。比如但丁的《神曲》或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所表现的世界都全
是想象的,虚构的,从科学观点看,都是不真实的。但是在这虚构的
世界中,一切人物情境仍是入情入理,使人看到不觉其为虚构,这就
是“诗的真理”。凡是艺术作品大半是虚构(fiction),但同时也都是
名学家所说的假然判断(hypothetical judgment)。例如,“泰山为人”
本不真实,但是“若泰山为人,则泰山有死”则有真实。艺术的虚构
大半也是如此,都可以归纳成“若甲为乙,则甲为丙”的形式,我们
不应该从科学观点讨论甲是否实为乙,只应问在“甲为乙”的假定之
下,甲是否有为丙的可能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执即起于此种分
别。柏拉图见到“甲为乙”是虚构,便说诗无真理;亚里士多德见到
32 西南联大美学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