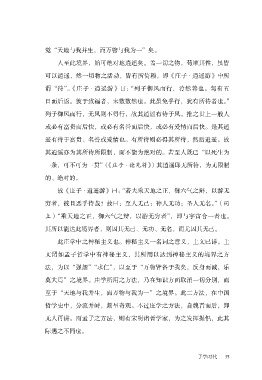Page 51 - 2021
P. 51
觉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矣。
人至此境界,始可绝对地逍遥矣。盖一切之物,苟顺其性,虽皆
可以逍遥,然一切物之活动,皆有所倚赖,即《庄子 · 逍遥游》中所
谓“待”。《庄子 · 逍遥游》曰:“列子御风而行,泠然善也。旬有五
日而后返。彼于致福者,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,犹有所待者也。”
列子御风而行,无风则不得行,故其逍遥有待于风。推之世上一般人
或必有富贵而后快,或必有名誉而后快,或必有爱情而后快。是其逍
遥有待于富贵、名誉或爱情也。有所待则必得其所待,然后逍遥。故
其逍遥亦为其所待所限制,而不能为绝对的。若至人既已“以死生为
一条,可不可为一贯” (《庄子 · 德充符》)其逍遥即无所待,为无限制
的、绝对的。
故《庄子 · 逍遥游》曰:“若夫乘天地之正,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
穷者,彼且恶乎待哉?故曰:至人无己;神人无功;圣人无名。” (同
上) “乘天地之正,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者”,即与宇宙合一者也。
其所以能达此境界者,则因其无己、无功、无名,而尤因其无己。
此庄学中之神秘主义也。神秘主义一名词之意义,上文已详。上
文谓如孟子哲学中有神秘主义,其所用以达到神秘主义的境界之方
法,为以“强恕”“求仁”,以至于“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,乐
莫大焉”之境界。庄学所用之方法,乃在知识方面取消一切分别,而
至于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之境界。此二方法,在中国
哲学史中,分流并峙,颇呈奇观。不过庄学之方法,自魏晋而后,即
无人再讲。而孟子之方法,则有宋明诸哲学家,为之发挥提倡,此其
际遇之不同也。
子学时代 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