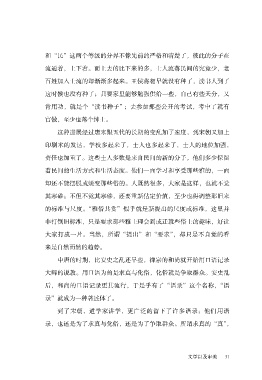Page 51 - 2020
P. 51
和“民”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,彼此的分子在
流通着,上下着。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,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,老
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。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,读书人到了
这时候也没有种了;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,自己有些天分,又
肯用功,就是个“读书种子”;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,考中了就有
官做,至少也落个绅士。
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,到宋朝又加上
印刷术的发达,学校多起来了,士人也多起来了,士人的地位加强,
责任也加重了。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,他们多少保留
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。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,一面
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。人既然很多,大家是这样,也就不觉
其寒碜;不但不觉其寒碜,还要重新估定价值,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
的标准与尺度。“雅俗共赏”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,这里并
非打倒旧标准,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,好让
大家打成一片。当然,所谓“提出”和“要求”,都只是不自觉的看
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。
中唐的时期,比安史之乱还早些,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
大师的说教。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,化俗就是争取群众。安史乱
后,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,于是乎有了“语录”这个名称,“语
录”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。
到了宋朝,道学家讲学,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;他们用语
录,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,还是为了争取群众。所谓求真的“真”,
文学以及审美 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