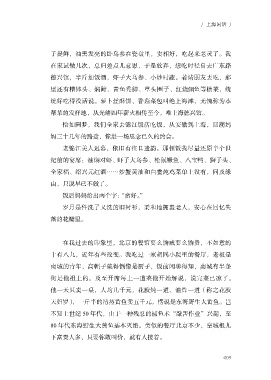Page 23 - 1964
P. 23
/ 上海闲话 /
子提鲜,油黑发亮的卧乌参在瓷盘里,卖相好,吃起来老灵了。我
在家试做几次,总归差点儿意思,于是放弃,想吃时径自去广东路
德兴馆,半斤加饭酒,虾子大乌参、小炒时蔬。若请朋友去吃,那
里还有糟钵头、焖蹄、青鱼秃肺、草头圈子、红烧 鱼等横菜,统
统好吃得没话说。萝卜丝酥饼、香菇菜包叫绝上海滩,无愧称为本
帮菜的发祥地,从光绪四年薪火相传至今,唯上海德兴馆。
恰如圆梦,我们全家去锦江饭店吃饭,从安徽到上海,回溯妈
妈三十几年的路途,像赴一场思念已久的约会。
老锦江美人迟暮,依旧有往日遗韵。那顿饭我尽量还原半个世
纪前的宴席:油焖对虾、 虾子大乌参、松鼠鳜鱼、八宝鸭、狮子头、
全家福、绍兴元红酒……炒蟹黄油和白鲞炖鸡菜单上没有,问及缘
由,只说早已不做了。
饭后妈妈给出两个字:“蛮好。”
岁月是件洗了又洗的旧衬衫,柔和地拥裹老人,安心在回忆失
落的花瓣里。
在我过去的印象里,北京的餐馆要么齁咸要么齁贵,不如意的
十有八九,近年有些改变。我吃过一家胡同小院里的餐厅,老板是
南城的青年,高帽子戴得倒像是厨子,饭前闲聊得知,南城有半条
街是他祖上的。及至开席每上一道菜他开始解说,说完菜已凉了。
他一天只卖一桌,人均几千元,花胶炖一道、油炸一道(称之花胶
天妇罗),一斤半的清蒸黄鱼卖五千元,愣说是东海野生大黄鱼。岂
不知上世纪 50 年代,由于一种残忍的捕鱼术“敲罟作业”兴起,至
80 年代东海野生大黄鱼基本灭绝。类似的餐厅北京不少,皇城根儿
下富贵人多,只要你敢叫价,就有人接着。
0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