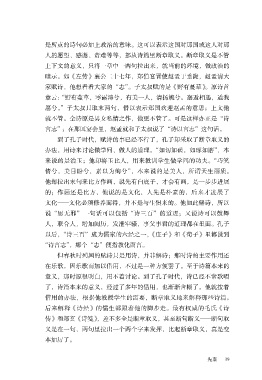Page 61 - 1957
P. 61
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。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
人的愿望、感谢、责难等等,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是不管
上下文的意义,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,就当前的环境,做政治的
暗示。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七年,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,赵孟请大
家赋诗,他想看看大家的“志”。子太叔赋的是《野有蔓草》。原诗首
章云: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兮,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邂逅相遇,适我
愿兮。”子太叔只取末两句,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;上文他
就不管。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,他更不管了。可是这样办正是“诗
言志”;在那回宴会里,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“诗以言志”这句话。
到了孔子时代,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,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
办法,用诗来讨论做学问、做人的道理。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,本
来说的是治玉;他却将玉比人,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功夫。“巧笑
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”,本来说的是美人,所谓天生丽质。
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,说先有白底子,才会有画,是一步步进展
的;作画还是比方,他说的是文化,人先是朴素的,后来才进展了
文化——文化必须修养而得,并不是与生俱来的。他如此解诗,所以
说“思无邪”一句话可以包括“诗三百”的道理;又说诗可以鼓舞
人,联合人,增加阅历,发泄牢骚,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。孔子
以后,“诗三百”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,《庄子》和《荀子》里都说到
“诗言志”,那个“志”便指教化而言。
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,并非解诗;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
在乐歌,因乐歌而加以借用,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。至于诗篇本来的
意义,那时原很明白,用不着讨论。到了孔子时代,诗已经不常歌唱
了,诗篇本来的意义,经过了多年的借用,也渐渐含糊了。他就按着
借用的办法,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,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。
后来解释《诗经》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。最有权威的毛氏《诗
传》和郑玄《诗笺》,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,甚至断句断义——断句取
义是在一句、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,比起断章取义,真是变
本加厉了。
先秦 3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