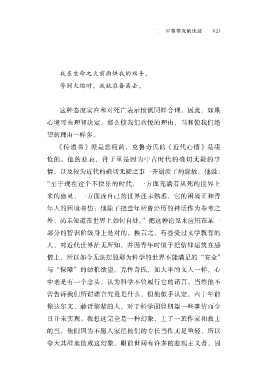Page 47 - 1935
P. 47
二 罗曼蒂克的忧郁 023
我在生命之火前面烘我的双手,
等到火熄时,我就准备离去。
这种态度实在和对死亡表示愤慨同样合理。因此,如果
心境可由理智决定,那么使我们欢悦的理由,当和使我们绝
望的理由一样多。
《传道书》派是悲痛的,克鲁奇氏的《近代心情》是凄
怆的。他的悲哀,骨子里是因为中古时代的确切无疑的事
情,以及较为近代的确切无疑之事一齐崩溃了的缘故。他说:
“至于现在这个不快乐的时代,一方面充满着从死的世界上
来的幽灵,一方面连自己的世界还未熟悉,它的困境正和青
年人的困境相仿:他除了把童年所曾经历的神话作为参考之
外,尚未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自处。”把这种论见来应用在某一
部分的智识阶级身上是对的。换言之,有些受过文学教育的
人,对近代世界茫无所知,并因青年时惯于把信仰建筑在感
情上,所以如今无法摆脱那为科学的世界不能满足的“安全”
与“保障”的幼稚欲望。克鲁奇氏,如大半的文人一样,心
中老是有一个念头,认为科学不曾履行它的诺言。当然他不
曾告诉我们所谓诺言究竟是什么,但他似乎认定,六十年前
像达尔文、赫胥黎辈的人,对于科学固曾期望一些事情而今
日并未实现。我想这完全是一种幻象,上了一班作家和教士
的当,他们因为不愿人家把他们的专长当作无足重轻,所以
夸大其辞地助成这幻象。眼前世间有许多的悲观主义者,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