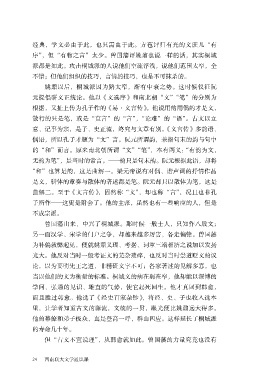Page 46 - 1957
P. 46
经典,学文必由于此,也只需由于此。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“有
序”,但“有物之言”太少。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,其实桐城
派都是如此。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,说他们范围太窄,全
不错;但他们组织的技巧,言情的技巧,也是不可抹杀的。
姚鼐以后,桐城派因为路太窄,渐有中衰之势。这时候仪征阮
元提倡骈文正统论。他以《文选序》和南北朝“文”“笔”的分别为
根据,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《易·文言传》。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,
散行的只是笔,或是“直言”的“言”,“论难”的“语”。古文以立
意、记事为宗,是子、史正流,终究与文章有别。《文言传》多韵语、
偶语,所以孔子才题为“文”言。阮元所谓韵,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
的“和”而言。原来南北朝所谓“文”“笔”,本有两义:“有韵为文,
无韵为笔”,是当时的常言。——韵只是句末韵。阮元根据此语,却将
“和”也算是韵,这是曲解一。梁元帝说有对偶、谐声调的抒情作品
是文,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。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,这是
曲解二。至于《文言传》,固然称“文”,却也称“言”,况且也非孔
子所作——这更是附会了。他的主张,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,但是
不成宗派。
曾国藩出来,中兴了桐城派。那时候一般士人,只知作八股文;
另一面汉学、宋学的门户之争,却越来越多厉害,各走偏锋。曾国藩
为补偏救弊起见,便就姚鼐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
光大。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,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
论,以为要明先王之道,非精研文字不可;各家著述的见解多寡,也
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。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,他却能以深博的
学问、弘通的见识、雄直的气势,使它起死回生。他才真回到韩愈,
而且胜过韩愈。他选了《经史百家杂钞》,将经、史、子也收入选本
里,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,文统的一贯,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。
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,真是登高一呼,群山四应。这样延长了桐城派
的寿命几十年。
但“古文不宜说理”,从韩愈就如此。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
24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