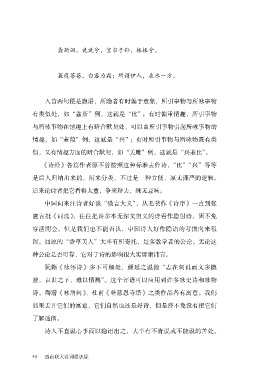Page 60 -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
P. 60
螽斯羽,诜诜兮,宜尔子孙,振振兮。
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;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
入首两句便是隐语,所隐者有时偏于意象,所引事物与所咏事物
有类似处,如“螽斯”例,这就是“比”;有时偏重情趣,所引事物
与所咏事物在情趣上有暗合默契处,可以由所引事物引起所咏事物的
情趣,如“蒹葭”例,这就是“兴”;有时所引事物与所咏物既有类
似,又有情趣方面的暗合默契,如“关雎”例,这就是“兴兼比”。
《诗经》各篇作者原不曾按照这种标准去作诗,“比”“兴”等等
是后人归纳出来的,用来分类,不过是一种方便,原无谨严的逻辑。
后来论诗者把它看得太重,争来辩去,殊无意味。
中国向来注诗者好谈“微言大义”,从毛苌作《诗序》一直到张
惠言批《词选》,往往把许多本无深文奥义的诗看作隐射诗,固不免
穿凿附会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,中国诗人好作隐语的习惯向来很
深。屈原的“香草美人”大半有所寄托,是多数学者的公论。无论这
种公论是否可靠,它对于诗的影响很大实毋庸讳言。
阮籍《咏怀诗》多不可解处,颜延之说他“志在刺讥而文多隐
避,百世之下,难以情测”。这个评语可以应用到许多咏史诗和咏物
诗。陶潜《咏荆轲》、杜甫《登慈恩寺塔》之类作品各有寓意。我们
如果丢开它们的寓意,它们自然也还是好诗,但是终不免没有把它们
了解透彻。
诗人不直说心事而以隐语出之,大半有不肯说或不能说的苦处。
40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