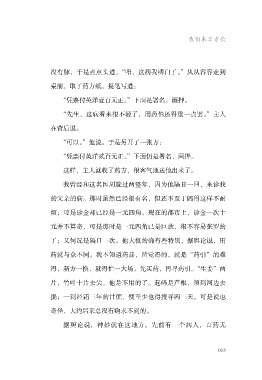Page 35 - 1952
P. 35
我们来日方长
没有脉,于是点点头道,“唔,这病我明白了。”从从容容走到
桌前,取了药方纸,提笔写道:
“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。”下面是署名,画押。
“先生,这病看来很不轻了,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。”主人
在背后说。
“可以。”他说。于是另开了一张方:
“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。”下面仍是署名,画押。
这样,主人就收了药方,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。
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,因为他隔日一回,来诊我
的父亲的病。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,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
烦;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。现在的都市上,诊金一次十
元并不算奇,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,很不容易张罗的
了;又何况是隔日一次。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,据舆论说,用
药就与众不同。我不知道药品,所觉得的,就是“药引”的难
得,新方一换,就得忙一大场。先买药,再寻药引。“生姜”两
片,竹叶十片去尖,他是不用的了。起码是芦根,须到河边去
掘;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,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。可是说也
奇怪,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。
据舆论说,神妙就在这地方。先前有一个病人,百药无
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