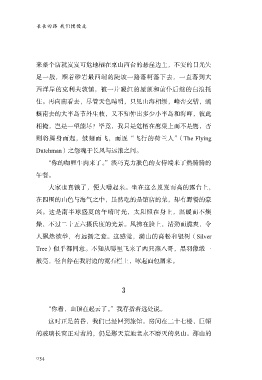Page 50 - 2009
P. 50
长长的路 我们慢慢走
来整个店就岌岌可危地栖在桌山西台的悬崖边上,不安的目光失
足一般,顺着砂岩最西端的陡坡一路落啊落下去,一直落到大
西洋岸的克利夫敦镇,被一片暖红的屋顶和前仆后继的白浪托
住。再向南看去,尽管天色晴明,只见山海相缪,峰峦交错,蜿
蜒南去的大半岛节外生枝,又不知伸出多少小半岛和海岬,彼此
相掩,岂是一望能尽?毕竟,我只是危栖在鹰巢上而不是鹰,否
则将腾身而起,鼓翅而飞,而逐“飞行的荷兰人”(The Flying
Dutchman)之怨魂于长风与远浪之间。
“你的咖喱牛肉来了。”淡巧克力肤色的女侍端来了热腾腾的
午餐。
大家也真饿了,便大嚼起来。坐在这么岌岌而高的露台上,
在四围的山色与海气之中,虽然吃的是馆店的菜,却有野餐的豪
兴。这是南半球盛夏的午晴时光,太阳照在身上,温暖而不燠
燥,不过二十五六摄氏度的光景。风拂在脸上,清劲而脆爽,令
人飘然欲举,有远扬之意。这感觉,满山的高松和银树(Silver
Tree)似乎都同意。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两只燕八哥,黑羽像缎一
般亮,径自停在我肘边的宽石栏上,啄起面包屑来。
3
“你看,山顶在起云了。”我存指着远处说。
这时正是黄昏,我们已经回到旅馆。房间在二十七楼,巨幅
的玻璃长窗正对着的,仍是那天荒地老永不磨灭的桌山。那山的
03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