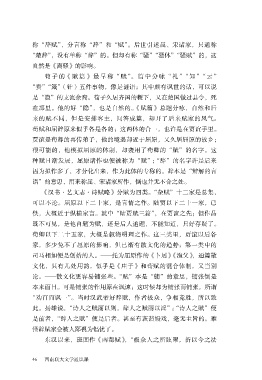Page 68 - 1957
P. 68
称“辞赋”,分言称“辞”和“赋”。后世引述屈、宋诸家,只通称
“楚辞”,没有单称“辞”的。但却有称“骚”“骚体”“骚赋”的,这
自然是《离骚》的影响。
荀子的《赋篇》最早称“赋”。篇中分咏“礼”“知”“云”
“蚕”“箴”(针)五件事物,像是谜语;其中颇有讽世的话,可以说
是“隐”的支流余裔。荀子久居齐国的稷下,又在楚国做过县令,死
在那里。他的好“隐”,也是自然的。《赋篇》总题分咏,自然和后
来的赋不同,但是安排客主,问答成篇,却开了后来赋家的风气。
荀赋和屈辞原来似乎各是各的;这两体的合一,也许是在贾谊手里。
贾谊是荀卿的再传弟子,他的境遇却近于屈原,又久居屈原的故乡;
很可能的,他模拟屈原的体制,却袭用了荀卿的“赋”的名字。这
种赋日渐发展,屈原诸作也便被称为“赋”;“辞”的名字许是后来
因为拟作多了,才分化出来,作为此体的专称的。辞本是“辩解的言
语”的意思,用来称屈、宋诸家所作,倒也并无不合之处。
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分赋为四类。“杂赋”十二家是总集,
可以不论。屈原以下二十家,是言情之作。陆贾以下二十一家,已
佚,大概近于纵横家言。就中“陆贾赋三篇”,在贾谊之先;但作品
既不可见,是他自题为赋,还是后人追题,不能知道,只好存疑了。
荀卿以下二十五家,大概是叙物明理之作。这三类里,贾谊以后各
家,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响,但已渐有散文化的趋势;第一类中的
司马相如便是创始的人。——托为屈原作的《卜居》《渔父》,通篇散
文化,只有几处用韵,似乎是《庄子》和荀赋的混合体制,又当别
论。——散文化更容易铺张些。“赋”本是“铺”的意思,铺张倒是
本来面目。可是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;这时候却为铺张而铺张,所谓
“劝百而讽一”。当时汉武帝好辞赋,作者极众,争相竞胜,所以致
此。扬雄说,“诗人之赋丽以则,辞人之赋丽以淫”;“诗人之赋”便
是前者,“辞人之赋”便是后者。甚至有诙谐嫚戏,毫无主旨的。难
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。
东汉以来,班固作《两都赋》,“极众人之所眩曜,折以今之法
46 西南联大文学通识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