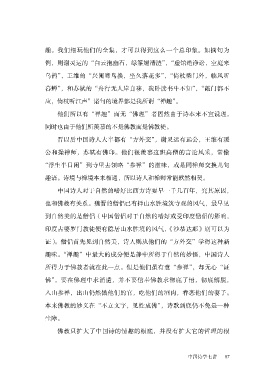Page 107 - 西南联大诗词通识课
P. 107
趣。我们细玩他们的全集,才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总印象。如摘句为
例,则谢灵运的“白云抱幽石,绿筿媚清涟”,“虚馆绝诤讼,空庭来
乌鹊”,王维的“兴阑啼鸟换,坐久落花多”,“倚杖柴门外,临风听
暮蝉”,和苏轼的“舟行无人岸自移,我卧读书牛不知”,“敲门都不
应,倚杖听江声”诸句的境界都是我所谓“禅趣”。
他们所以有“禅趣”而无“佛理”者固然由于诗本来不宜说理,
同时也由于他们所羡慕的不是佛教而是佛教徒。
晋以后中国诗人大半都有“方外交”,谢灵运有远公,王维有瑗
公和操禅师,苏轼有佛印。他们很羡慕这班高僧的言论风采,常偷
“浮生半日闲”到寺里去领略“参禅”的滋味,或是同禅师交换几句
趣语。诗境与禅境本来相通,所以诗人和禅师常能默然相契。
中国诗人对于自然的嗜好比西方诗要早一千几百年,究其原因,
也和佛教有关系。魏晋的僧侣已有择山水胜境筑寺观的风气,最早见
到自然美的是僧侣(中国僧侣对于自然的嗜好或受印度僧侣的影响,
印度古婆罗门教徒便有隐居山水胜境的风气,《沙恭达那》剧可以为
证)。僧侣首先见到自然美,诗人则从他们的“方外交”学得这种新
趣味。“禅趣”中最大的成分便是静中所得于自然的妙悟,中国诗人
所得力于佛教者就在此一点。但是他们虽有意“参禅”,却无心“证
佛”,要在佛理中求消遣,并不要信奉佛教求彻底了悟,彻底解脱,
入山参禅,出山仍然做他们的官,吃他们的酒肉,眷恋他们的妻子。
本来佛教的妙义在“不立文字,见性成佛”,诗歌到底仍不免是一种
尘障。
佛教只扩大了中国诗的情趣的根底,并没有扩大它的哲理的根
中国诗学七讲 8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