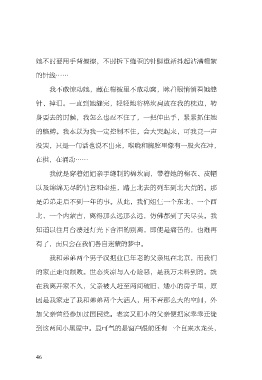Page 64 - 2043
P. 64
她不时要用手背擦擦,不时拆下缝歪的针脚重新抖起沾满棉絮
的针线……
我不敢惊动她,藏在棉被里不敢动窝,眯着眼悄悄看她缝
针、掉泪。一直到她缝完,轻轻地将棉坎肩放在我的枕边,转
身要去的时候,我怎么也忍不住了,一把伸出手,紧紧抓住她
的胳膊。我本以为我一定控制不住,会大哭起来,可我竟一声
没哭,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喉咙和胸腔里像有一股火在冲,
在拱,在涌动……
我就是穿着姐姐亲手缝制的棉坎肩,带着她的棉衣、皮帽
以及绵绵无尽的情意和牵挂,踏上北去的列车到北大荒的。那
是弟弟走后不到一年的事。从此,我们姐仨一个东北、一个西
北、一个内蒙古,离得那么远那么远,仿佛都到了天尽头。我
知道以往月台凄迷灯光下含泪的别离,即使是痛苦的,也难再
有了,而只会在我们各自迷蒙的梦中。
我和弟弟两个男子汉把业已年老的父亲甩在北京,而我们
的家正走向颓败。世态炎凉与人心险恶,是我万未料到的。就
在我离开家不久,父亲被人赶至两间破旧、矮小的房子里,原
因是我家走了我和弟弟两个大活人,用不着那么大的空间,外
加父亲曾经参加过国民党。老实又胆小的父亲便把家乖乖迁徙
到这两间小黑屋中。最可气的是窗户跟前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,
4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