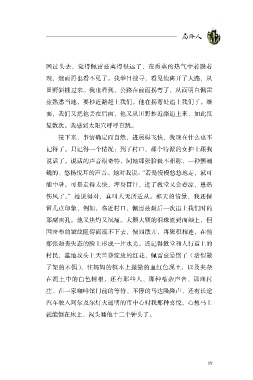Page 37 - 2138
P. 37
回过头去,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,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
现,继而再也看不见了。我举目搜寻,看见他离开了大路,从
田野斜插过来。我也看到,公路在前面拐弯了,从而明白佩雷
兹熟悉当地,要抄近路赶上我们。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。继
而,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,他又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,如此反
复数次。我感到太阳穴呼呼直跳。
接下来,事情确定而自然,进展得飞快,我现在什么也不
记得了。只记得一个情况:到了村口,那个特派的女护士跟我
说话了。说话的声音很奇特,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,一种颤巍
巍的、悠扬悦耳的声音。她对我说:“若是慢慢悠悠地走,就可
能中暑。可是走得太快,浑身冒汗,进了教堂又会着凉,患热
伤风了。”她说得对,真叫人无所适从。那天的情景,我还保
留几点印象,例如,临近村口,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
那副面孔。他又焦灼又沉痛。大颗大颗的泪珠流到面颊上,但
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,便四散开,再聚积相连,在他
那张颓丧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。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
村民,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,佩雷兹晕倒了(活似散
了架的木偶),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,以及夹杂
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,还有那些人、那种嘈杂声音、那座村
庄、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、不停的马达隆隆声,还有长途
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,心想马上
就能倒在床上,闷头睡他十二个钟头了。
19